“群里的老师们,有认识这个蘑菇的吗?我们这边有几个云南籍的务工人员在山上采食蘑菇后中毒了。”
5月底的一个求救信息,在“广西毒蘑菇鉴定群”里炸开了锅。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李海蛟看到照片后立刻回复:“硬皮马勃属的,胃肠炎型毒蘑菇,有些伴有一定的神经毒性,不是剧毒的。”
就在大家松了口气时,两小时后群里另一张照片让李海蛟瞬间警惕:“这是剧毒的灰花纹鹅膏!有几人中毒?”
每年到这个时候,这样的紧张时刻总会在全国十几个“毒蘑菇群”里反复上演。作为食源性疾病中致死率最高的“杀手”,毒蘑菇的致命案例占比超过50%,而今年国内已有近10人因此丧命。
在李海蛟的实验室里,来自全国各地的毒蘑菇样本堆积如山。其中出镜率最高的是大青褶伞,每年能 “承包” 1/4 到 1/3 的中毒事件。此外,剧毒鹅膏、近江粉褶蕈、日本红菇、斑褶菇、牛肝菌等都是常见 “凶手”。
李海蛟曾参与国内2000余起蘑菇中毒事件的处置,每次得知中毒事件后,除了远程为蘑菇识别和救治提供建议,他也会让地方疾控中心将导致中毒的蘑菇样品邮寄到中疾控位于北京的实验室。“如果患者手头有导致中毒的样品,或者能给出采集位置,当地疾控会去采集样品,烘干之后寄给我们,由我们做后续的鉴定工作。”李海蛟说。

致命鹅膏。
2024年,李海蛟参与了《中国毒蘑菇新修订名录》的发表工作,这项修订工作由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图力古尔主持,系统总结了我国大型真菌调查的成果,盘点、更新了我国的毒蘑菇状况。
2025年,来自东北、华北、华中、华南、西南的五位真菌研究学者基于更新名录,以及在实际救助指导中积累的丰富诊治经验,共同编著了《中国的毒蘑菇》一书。书中详尽介绍了我国已知的毒蘑菇物种及中毒后的救治方法,满足大众科普需求的同时,也为疾控人员和医护人员提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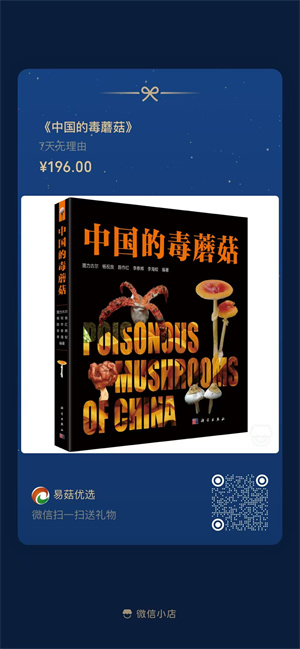
扫码购买
然而,每年的蘑菇中毒事件仍然高发。以2024年为例,食源性疾病监测系统共报告了2800多起蘑菇中毒事件,涉及9000多人中毒,39人死亡。
在蘑菇中毒事件高发地区,采食蘑菇的行为仿佛刻在了当地人的基因里。“事实上,每年的蘑菇中毒案例,多数是山区百姓在采摘后误食所致。”杨祝良强调。
还有一些自认为具备识别蘑菇经验的人,他们中毒的比例同样很高。“尤其是当科学知识与老百姓的传统经验发生冲突的时候,很多老百姓宁愿相信自己的经验是对的。”李海蛟常说,不能盲目地相信所谓的经验,这也是科普工作中的难点。
有的网友尝试用人工智能(AI)识别、区分蘑菇,但李海蛟解释,蘑菇大多为伞菌,由菌盖和菌柄构成,可辨识的特征点极为有限,外观又极为相似,不像植物有根、茎、叶、花、果,可辨识的特征很多。目前蘑菇物种的AI识别技术尚不成熟,国内也暂未开发相关的识别软件。

可食的草鸡枞鹅膏(左)和剧毒的灰花纹鹅膏(右)。

可食的稀褶红菇(左)与剧毒的亚稀褶红菇(右)。受访者供图
在李海蛟看来,毒蘑菇科普仍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那么,科普如何才能真正落实到那群采蘑菇的人?
如今各种专业的科普宣传视频、挂图、广播、条幅、游戏、讲座等“轰炸式”手段,也在深入偏远山区。比如,通过给山区中小学的孩子科普,孩子就可以告诉家里的大人,指出大人采蘑菇行为中的错误。“近些年,蘑菇中毒的死亡人数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李海蛟说。
此外,李海蛟还强调关于蘑菇的生态科普。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种“网红”旅游项目——“捡菌团”活动。这种新式采蘑菇活动因“爆框”“打卡”“出片”被追捧,但背后是游客对蘑菇生长地的“掠夺式”扫荡。网络上频频有人指出,在这种破坏性采集之下,蘑菇都快被采光了。
李海蛟说,许多蘑菇是森林中的降解者,是森林物质和能量循环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序采集是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因此,我们强烈呼吁大家不要盲目到野外采蘑菇,建议以观察、欣赏、学习为主。”













